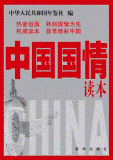热点推荐
- ·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北京常住人口1961
- ·家具厂因缺乏灭火设施起火燃烧5小时(
- ·北京28家老字号签责任书拒绝非法添加
- ·志愿者京哈高速截车救狗续:部分获救
- ·地税局干部受贿186万获刑10年半--中
- ·零点原主唱周晓鸥以乐队名义宣传遭索
- ·人大常委执法检查组建议修改老年人权
- ·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抵北京开始
- ·夫妻建数据库倒卖个人信息--中国国情
- ·公安部将在全国开展清剿火患行动遏制
- ·超市老板退货不成打伤送货员--中国国
- ·男子买小产权房被判无效 起诉房主讨
- ·北京职工获全国五一奖章将获万元奖金
- ·个税修正草案未表决 公众普遍认为300
- ·3辆公交车连环追尾致5名乘客受伤(图)
- ·上门女婿不愿离婚杀妻后自残(图)--中
相关链接
- ·北京地铁2号线因信号故障双向受阻--
- ·北京月底调整汽油标号 90号93号97号
- ·北京市主要网站斥巨资购买版权--中国
- ·北京多地为降低PM2.5加设检查岗查尾
- ·北京首发PM2.5日均值 专家称有利评价
- ·街道办主任微博与居民互动 处理房屋
- ·博士生以实验室研发情景剧 花500元自
- ·4岁女童被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路过老人
- ·女子6次谎称怀上孩子骗情人300万--中
- ·女孩与同性恋网友见面遭强制猥亵--中
- ·小伙手捧鲜花地铁求婚遭拒后昏厥(图)
- ·北京天坛祭天使用唯一指定用酒引争议
- ·疑犯在地铁关门瞬间抢走乘客手机--中
- ·北京站今日拆除临时售票处(图)--中国
- ·北大校长周其凤称中国教育很成功--中
入编邀请更多>>

2010版国情
北京安化楼厨房反映大楼历史变迁--中国国情手册
2011-09-05
日子继续过下去,厨房像是放大镜,映着大楼里的历史变迁。
“文革”期间,厨房成了批斗的地方,小将们把“走资派”关进厨房,“打出了血”。过去并肩做饭的邻居开端相互躲避,“生怕对方是黑五类”。
改革开放后,楼里住户日杂,年青一代情愿在阳台摆个桌子放电磁炉也不愿走进大厨房。邻近的房屋中介业务员说,要是安化楼房间里能有厨房,房租起码高上500元。
老徐隔壁的邻居上世纪80年代进楼,那时轮班值日制度早已不复存在,值日牌不知道被谁丢进了垃圾桶。大厨房甚至成了楼道战斗的主战场:有人烧水丢了水壶,有人撞见自家煤气灶被别人拧开做饭,还有人做了锅红烧肉,肉还没熟,一错眼珠连锅都被端走了。
大厨房里按人头收费的公共水表,更是最大的麻烦导火索:交水费时少报人头,在厨房里玩儿命用水,更有甚者,直接把自家的洗衣机推到厨房。
为了缓解居民的怨气,2008年,房管所停用了公共水表,改为在厨房里的公共水池安装了一字排开的水表和水龙头,供各户自用。共住一个单元的两户人家也分了表,在墙上用红油漆刷上房间号,再标上“大”和“小”加以区分。
然而换了水表后,一些水龙头被挂上了密码锁,另一些阀门则层层包上了塑料袋,还有的住户索性把自家的水龙头卸下来,再把水管封死,“还不是怕别人家偷自己的水”。
公共厨房里没有抽油烟机,弥漫着一股庞杂而刺鼻的味道。厨房的地面被油垢笼罩,踩在上面有显著的黏稠感。蹲下身,角落处能找到一些指甲盖大的蟑螂,仰着身黏在油垢里。
“现在厨房可比厕所脏多了。”正在做饭的老徐把苦瓜扒拉进锅里,低着头说。
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老徐记得,大楼里最初的时光,不是这个样子的。
“老主任在长长的过道里喊一句,清除啦!你就看吧,一个个儿的人头都从门里冒了出来。”他把热好的苦瓜放下,带着浓重的江苏口音模拟起当年李秀梅喊人的样子。
那时的广渠门内一带,还只是成片的菜园子和乱葬岗,但大楼里似乎别有洞天。
楼里的孩子们拿电梯当玩具,刚把他们送到九层,一开八楼的门,便又在那儿候着了。但也有孩子会因为楼太大且各层长得都一样而迷路,便抱着书包蹲在楼道哇哇大哭。
大人们则爱好聚在九层的活动室里下棋,除了围棋和象棋,还经常玩一种从苏联传入的克朗棋。每逢国庆节,楼里楼外的街坊们便都上到九层,“那天安门的烟花,看得真真儿的”。
但这份镇静的时光为期不长。“文革”中,住在楼里的红卫兵小将们将大字报贴满全楼,连各家的凳子也不放过。姚瑞云记得,自己年青时在上海照相馆拍的英俊照片被销毁了,每层都有的5盏大型玻璃吊灯也被砸烂。很快,楼里一些成分不好的人被揪了出来,其中还包含一个曾经的军统特务。
“人与人之间的信赖被撕碎了。”徐钦敏回想,正是从那时候开端,“大楼里的人互相之间开端不闻不问,谁也不敢接近谁。”
做厂长的老徐没有躲过那个年代。在单位里,人们在他身前点上火堆,烤得他浑身冒汗;往他打仗时留下子弹的胯骨猛踹;带着他游街,有时候走到安化楼邻近,楼里的小孩就跟在后面看热闹。
邻居们说,老徐的大儿子当时才12岁,因为不堪学校里同学的辱骂,在家里的木板床上自杀。在牛棚劳教的老徐疯了一样地赶回家,当街拦了一辆大公共,送昏迷的儿子去医院。但孩子最终也没有醒过来。
安化楼不只出过这一条人命。五层一个被认定是“黑五类子女”的小伙子,跳楼而死。另一个女孩子,也从楼上一跃而下。
上世纪70年代末,老徐获平反。80年代末,老徐退休。市场经济的大潮里,楼里的下一代也长大了。
一个叫狗子的孤儿靠给小卖部搬货保持生计,后来帮人贩卖水果,再后来自己开了运输公司,搬离了安化楼。另一个老徐从小看大的孩子,靠在旧货市场卖古董买了一幢楼。
老徐曾经对他们说:“你们99%不如我,只有1%比我厉害,就是会捞钱。”
10年前,大楼对面的平房群变成了一个叫“富贵园”的高级住宅区,房价节节攀升。但安化楼仍然属于房管所的公房,不许可买卖。
一些老住户搬进了对面的小区,但分开的人从不放弃楼里的公房,给房管所交的租金每月100多元,但转手租出去却是十几倍的价钱。如今,楼里三分之二的住户都是二道或三道租客。
“现在楼里的人就像是山药蛋。山药蛋你知道吗?就是一个一个互相不挨着。”老徐叹气道。
没人说得清从什么时候开端,楼道里挤满了旧纸箱、拖把,以及舍不得扔的破家具。原来两辆自行车能并排通过的大楼道,如今已经容不下两个人错身。据说,1998年安化楼大清算时,总共从楼道里拉走了100多车垃圾。
“这破庙似的楼从来没人整修过,房租倒从5块钱涨到了100多。”大厅里,一个穿着跨栏背心的老爷子已经摇着扇子埋怨了半天,正跟旁边蹲着的一个二道租客念叨,“不对,华国锋的时候落过4块钱。”
“为什么落啊?”年青的租客将身子往前倾了一下。
“为什么落,我哪知道为什么落?你告知告知我,现在物价为什么涨啊?”
老爷子合起折椅,拍拍屁股扭头就走,“放炮完毕,走人!”
老徐则在一旁闷头看着报纸。他订了5份报,每天看,但很多时候还是认为自己“怎么都跟不上形势”。
他眼看着,大楼明明是公房,却被一些租户私卖出去,到房管所托托关系就能转让出租权。他也想过调查一下,“举报他们”,但最后还是认为算了,“到头来枪口还是对着我自己”。
想不通的还有国家大事,“当初号令我们打倒大地主刘文彩,可现在那些‘地主’,比刘文彩大多了。”
因为怕自己“得了精力病”,老徐还曾特意去看过两次心理医生。
医生告知老徐,解决不了他的问题,建议他“去找中央党校的老师聊聊”。
“我们离死都不远了,还管这些干嘛呢?李主任你说呢?”老徐站了起来,问旁边的李秀梅。
“早被淘汰了,还什么主任不主任的。”李秀梅看有外人在,似乎有点不好意思。
尽管20年前就已经退休,她还是保持着每天下午给老住户们分发报纸和信件的习惯。7月末,她还组织了一次楼里老党员的集体活动,每个人为党的生日写一句祝福。
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了我
老人们偶尔会聊起,当年另外两座公社大楼,如今变成了什么样子,又发生着怎样的故事。
东城区的北官厅大楼早在2001年就在危房改造中被爆破拆除。据说,爆破在夜里进行,许多搬走的老街坊都专程回来跟老楼告别。出乎意料的是,大楼竟然有一个角没有炸掉,后来又用铲车铲了3天才拆清洁。老人们固执地以为,这是因为建大楼的资料是“全中国最好的”。
从2003年开端,位于西城区的福绥境大楼也传出了拆迁的消息。有人说拆迁是因为大楼被列为北京市第一重大火灾安全隐患,也有人说是因为“影响了白塔寺的风貌”,但更多的被拆迁者则信任,真正的原因是金融街的北扩。
如今的福绥境大楼里还剩下不到30户的坚守者。狭长昏暗的楼道里,很多房间已经被砌上了红砖,彻底封死。大楼旁的福绥境小学,如今也被并入官园小学。这座大楼甚至被人们叫做“鬼楼”,一到周末就有学生们到空荡荡的楼里去“探险”。
去年,这座早已不在新闻中涌现的老楼曾重新进入人们的视野。中央美院的一个学生以这栋大楼为底本完成了自己的毕业设计,主题是将其改造为专为“蚁族”群体而设的青年旅社。
让人印象深入的是,翻新的公社大楼里专门设计了一个发泄室,以及一个党支部办公室。
“我愿望为城市里的弱势群体做一点东西,而福绥境大楼的共产主义气质,吸引我把它当做改造原型。”设计者胡伟楠这样解释他的初衷。
不过他也表现,在金融街北扩的背景下,这个方案也许只是“又一个乌托邦”。
正是因为这个作品,胡伟楠已经被一家著名的建筑师事务所相中,而他将要投身的设计项目,是一个高端别墅群。
关于福绥境大楼的故事,安化楼里的老人感同身受。大楼建成时,周边还是土路,现在已经变成了被称为“第二长安街”的两广路;楼旁的坟头和菜园则变成了每平方米售价4万元以上的商业住宅区。
老人们埋怨,曾经是地标的九层大楼,如今只是个“矮胖子楼”,跟环境和时期都格格不入。
王守恒记得,自己女儿上学的时候,别人问她家住哪儿,她都会大声说,“安化楼啊!”到了孙辈,小外孙女却说什么也不愿意带朋友进楼了。
尽管大楼门前的公交站牌上仍保存着“安化楼”的站名,但它的确正在被人们遗忘。一个年青的租客说,打车回家,总要告知司机师傅“去富贵园小区对面”。
偶尔,这座大楼也会被人想起来。北京奥运会前夕,灰色的大楼被刷成了粉色。前几年,一部葛优主演的电影《卡拉是条狗》也在大楼里取景。谈起在这儿取景的原因,李秀梅轻声说:“破呗。”
去年,一位建筑师曾经探访过这里。分开之后,他在一篇手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当这一切消逝,他们最不容易调适的,将不是房价、房租、平米数,甚至不是地理位置,而是在大家一样贫穷也就等于一样富有的年代里才干享受的优胜感,将一去不复返。”
傍晚时分,斜阳覆盖着安化楼,拖出了长长的影子。
大楼老了。
门前多了一个可供轮椅通过的无障碍通道,电梯不再是三层以下不停,外墙贴上了“大楼容易造成外墙灰皮脱落现象,敬请此楼及邻近居民不要在此停留”的告示。
设计大楼的人老了。
金诚伤感地说,能一起聊天的老同事越来越少,“前一天打完电话,后一天也许人就没了。”当年具体分管安化楼设计的建筑师叫张念真,已经在去年逝世。
大楼里曾经的年青人也老了。
王守恒的耳朵上已经戴了助听器;李秀梅的老伴儿逝世了,陪了她很多年的狗也在前年老死了;徐钦敏的妻子去年死于突发脑溢血,他自己也曾写好一封遗书,要求死后将遗体捐给医院或护士学校做研究。
晚上7点,老徐准时回到自己的小屋。他从微波炉里取出前一天蒸好的鲤鱼,坐在写字台前吃晚饭,并时不时地扭过火,关注电视机里的《新闻联播》。
这个狭窄的房间从来没有装修过,墙壁是蜡黄色,窗户玻璃裂了缝,墙上的钟也已经停掉不走。电视机顶上,摆着老两口的合照。
1960年底的一天,意气风发的北京机床电器厂厂长徐钦敏带着他的妻子、刚出身不久的儿子和一张木板床搬进了公社大楼。这个年青的共产党员信任,美妙的新生活就在眼前。(本版图片由张嘉妍摄)
欢迎发表评论我要评论
上一页 1 2 下一页
微博推举 | 今日微博热门(编辑:SN026)- 上一篇:北京查获1200余万元假汽车配件--中国国情 【加入收藏】
- 下一篇:北京西直门外大街路面塌陷(图)--中国国情网
相关链接
- 北京地铁2号线因信号故障双向受阻--中国国情
- 北京月底调整汽油标号 90号93号97号汽油将取消--中国
- 北京市主要网站斥巨资购买版权--中国国情手册
- 北京多地为降低PM2.5加设检查岗查尾气超标车--中国国
- 北京首发PM2.5日均值 专家称有利评价空气质量--中国国
- 街道办主任微博与居民互动 处理房屋漏水违建等--中国
- 博士生以实验室研发情景剧 花500元自拍6集短剧--中国
- 4岁女童被陌生男子强行抱走 路过老人将其救下--中国国
- 女子6次谎称怀上孩子骗情人300万--中国国情
- 女孩与同性恋网友见面遭强制猥亵--中国国情网
- 小伙手捧鲜花地铁求婚遭拒后昏厥(图)--中国国情网
- 北京天坛祭天使用唯一指定用酒引争议--中国国情网
- 疑犯在地铁关门瞬间抢走乘客手机--中国国情手册
- 北京站今日拆除临时售票处(图)--中国国情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