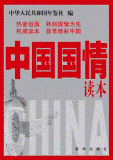热点推荐
- ·学者倡征移民税 遏内地孕妇补贴公院-
- ·他领着农民兄弟玩“资本魔方”--中国
- ·环球速递:法国巴黎银行首季营收超过
- ·做大融资渠道有利外储分流--中国国情
- ·浙江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启动--
- ·国际纸浆涨价不是应对重点--中国国情
- ·2011贸易金融发展高层研讨会主题--中
- ·索罗斯再次唱空中国经济 称治理失效
- ·“我倾向于强有力协调机制下的分开监
- ·去年外汇储备资产增加4696亿美元--中
- ·世行称移民汇款有力支持非洲发展--中
- ·胡润称中国10亿美元级别富豪达600位
- ·长江证券:反弹因素3月后将减弱 建议
- ·王岐山:信任不能代替监督 严厉打击
- ·鲍泰利:中国实现经济再平衡迫在眉睫
- ·券商直投再迎新军 年内将迎密集回报-
相关链接
入编邀请更多>>

2010版国情
一个美国人眼中的文明冲突--中国国情
2011-05-04
奥萨玛·本·拉登在巴基斯坦被美军击毙的消息,正在被全世界不同国家、不同信仰的人所热议。除了恐惧主义者这一身份,本·拉登更是一个符号,这个符号包括了千百年延续至今的宗教和文明的冲突
此时,一个美国人如何对待拉登之死?在他眼中,宗教与政治是什么关系?不同文明之间又是如何发生冲突的?《法治周末》记者采访了美国纽约州的史蒂夫·莫拉夫先生(SteveMoraff)一位从事软件开发的犹太裔美国人,他的家族从其曾祖父开端便在美国生活。莫拉夫先生的观点或许为我们供给了认识问题的另一种视角。
法治周末记者 李秀卿
《法治周末》:历经十年穷追不舍,美军突击队胜利击毙了世界头号恐惧分子本·拉登。获知这一消息后,作为一个美国人,你的第一感受是什么?你的朋友如何对待此事,他们以什么方法表达自己的心境?
史蒂夫·莫拉夫
(SteveMoraff):我对本·拉登的死讯反响很冷漠。对我来说,他对世界事务无关已有数年。在某种意义上,我以为小布什总统的卸任就是本·拉登的公开死亡。布什试图通过向美国人灌输本·拉登会卷土重来这一恐怖,以保护其总统的位置。当布什卸任时,本·拉登也失去了他获取著名度的主要来源。
奥巴马总统则更为务实。自他上任以后,拘捕或消灭本·拉登便成了一个悄无声息的目的,成了美国情报部门诸多任务中的一项。甚至奥巴马就拉登死亡所作的演讲也不是大话连篇。奥巴马总统是一个有耐烦的学术派,他不以为为晋升他的大众支撑率,有必要炫耀针对恐惧分子的每一桩成功。他正确地意识到选民会根据他工作的最后成果而不是今天暂时的情感来断定他。
有些美国人在大街上欢庆,好像这是某种体育盛事,他们甚至还唱我最爱好的一首歌皇后乐队的《我们是冠军》。我对此并不觉得光荣。我讨厌这首歌被用于这种情势。我认为唱这首歌的时候应当是驾驶国外产的车、耗费国外产的汽油、在美国宽敞的高速公路上高速开车、感到比任何东西都优胜而事实上周围一片空旷,没有人会因你的行为而难为情的时候,而且应甩开嗓门地唱。
《法治周末》:在“9·11”事件发生后的10年里,本·拉登一直是美国安全的重大威逼之一,现在本·拉登已死,你认为你的国家会因此而变得更加安全吗?
史蒂夫·莫拉夫:我以为美国在“9·11”之后变得更安全了,因为美国人如今意识到,这个国家也受到恐惧主义的威逼。然而,我以为对世界的最大袭击尚未到来,而且它们不大可能会发生在美国的土地上。我最担忧亚洲,因为这一大陆上有数目众多的核兵器。我倒愿望中国与俄罗斯追求一个无核的世界,我也愿望美国的政客们站起来,为他们对核兵器的支撑负责。
作为一个美国人,我看到过本来认为对美国友爱的专制政体很快就对美国翻脸。由专制者统治的小国不久便忘却谁是他们的朋友。它们能很快地背叛盟友,就像被宠坏了的孩子一样。我信任随着中国日益进入由总体善良的政府组成的国际大家庭,它会发现自己也会成为缺少这种稳固与合法性的政府及恐惧分子的敌人。
因此,尽管我不以为本·拉登的死亡是构成街头欢庆的原因,然而我确定不会惦念他,而且我以为世界上的许多人也不会。
《法治周末》:著名学者塞缪尔·P·亨廷顿著有《文明的冲突》一书,你以为,世界上确切存在着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吗?是以美国为主的西方文明或者价值观,与其他文明和价值观的冲突吗?你有这种感受吗?你对西方文明和价值观具有某种优胜感吗?
史蒂夫·莫拉夫:事实上,政客们尤其爱好文明之间的碰撞,普通人对这类事实不那么感兴致。美国人对这一问题的意见很特殊。1960年代和1970年代我还是孩子时,美国人曾畏惧一浪接一浪地追求美国财富和美妙生活的移民潮会涌入美国、席卷美国、并摧毁美国。
刚变得富有的人很自然地过火担忧人人都想掠夺他们的财富,而美国人作为一个群体也曾经有这种感到。然而在过去的20年中,我们当中很多对那些感受仍记忆犹新的人已逐渐意识到,剩下的世界正以与美国的致富模式雷同的方法辛苦的劳动变得充裕。大多数美国人信任对所有人都好的东西对美国人也同样好,因此美国人现在比许多年前焦虑畏惧的程度要轻一些。
美国人为美国在辅助世人方面以及对世界的贡献觉得骄傲,这种骄傲是正确的。在二战期间,美国既站在成功的一方,也站在正义的一方。尽管在冷战期间,美国与俄罗斯都从事了一些邪恶的勾当,然而随后美国一直朝着成为世界上一支仁慈权势的道路前进。我们美国人信任,我们的国家是一支仁慈的力气,而且我们也是这么要求我们的领导人的。
《法治周末》:在美国,宗教能够影响政治吗?或者说,宗教的文化和人性哲学在多大程度上对世俗政治产生了影响?
史蒂夫·莫拉夫:在美国,政客常常必需伪装他们真的信教,否则他们就难以当选。不过,曾有犹太人和穆斯林当选为美国国会议员,而且他们总是被作为大多数的基督教选民选上。在我看来,一个犹太人已经在2000年大选中被选为美国副总统(指大选中的副总统候选人、犹太裔参议员乔·利伯曼编者注),但是乔治·布什窃取了竞选成果。在那场竞选中人们都信任,实际上阿尔·戈尔和他的竞选伙伴乔·利伯曼博得了大部分选票。
然而,美国人也接收了美国事一个“犹太基督教”国的意见,鉴于伊斯兰教本身便继承了犹太—基督教的部分内容,甚至美国的穆斯林人也认同这一点。即便印度教及佛教等不那么风行的宗教,在美国也不受任何压迫。
另一方面,还存在一小部分美国人,他们宣称他们很严厉地信奉自己的宗教,并试图要求政府为他们的狭隘利益服务。政治家们常常伪装他们会为这些宗教利益效率,但是他们实际上并不真的关怀这部分美国人。
换言之,美国事个在教堂与政治之间有真实距离的世俗国家,用我们的话说,是一个真正的政教分别的国家。
《法治周末》:你以为,以美国为主的西方,为什么会与伊斯兰世界发生如此剧烈的冲突?事实上,在当今的伊斯兰世界,当年塔利班执政时代推行的极端思想,也不会得到主流的认可。拉登和他的塔利班成为极端的反美反西方权势,是宗教的冲突吗?
史蒂夫·莫拉夫:我不认为本·拉登那么仇恨美国和美国人民。本·拉登是个恐惧主义者,但更多的,他是个政治家,也是个白痴。他愿望给予西方国家在经济实力方面以致命的一击,并通过这一进程而名扬天下。但实际上,世贸中心大楼里都是来自不同国家的普通劳动者,他们做着平常的工作,与其他办公大楼的人别无二致。清算他制造的残骸、赔偿袭击的受害人、甚至以及重建那些大楼的总体成本对美国经济来说只是沧海一粟。
即使如此,本·拉登已经得到了他最想要的成为全世界最著名的人。在这一方面,本·拉登与焚烧《古兰经》的特里·琼斯如一丘之貉。如果你把他们俩同时锁在一间牢房里,他们可能直到死前的最后一刻都会很开心。
《法治周末》:在历史上发生的很多战斗中,有一部分是因为宗教的冲突引起,你以为多种宗教怎样才干和平相处?特殊是在美国这样的多宗教融会国家。
史蒂夫·莫拉夫:其实,历史上的宗教信徒曾在许多地方和平共处过。在美国,宗教冲突是一以贯之的政治问题。政客们关怀的其实不是宗教,而是政治权力。如果这些问题留给他们自己,勤劳普通的人们会和平地生活,关怀家人,邻里和气。
美国在这类差别中引领着世界,因为美国作为一个文化熔炉有很长一段历史了。对世界而言,美国可能给人以反穆斯林的印象,这是错误的。伊拉克战斗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人在是否支撑这场战斗的问题上看法不一,但不论哪方,都支撑并关怀伊拉克的人民。那些反对那场战斗的人要么是反对广泛的战斗,要么是认为美国须要先处置国内问题。支撑那场战斗的人则认为,为了将伊拉克人民从一种恐怖的暴政中解放,就义美国人的性命是值得的。只有很小比例的美国人想要这场战斗的原因是,他们以为油价会降低,或美国能从掌握伊拉克上获得某种利益。这些人可能包含了布什政府内部、想直接从这种利益中得到好处的某些人。
我个人几乎要支撑这一战斗行动了,只是那时我以为它还是个错误,因为它表明我们缺少耐烦。世界须要学会使用制裁和耐烦来解决这类冲突,而不是使用战斗。
《法治周末》:2010年9月11日,就在美国高低纪念"9·11"之际,被称为"猖狂牧师"的特里·琼斯却坚持要焚烧《古兰经》,人们担忧拥有15亿教众的伊斯兰教和20亿信徒的基督教之间将因此涌现紧张,更会将美国置于被报复的危险地步。现在来看,你如何评论这一不可思议的行为?
史蒂夫·莫拉夫:这一行动与基督教毫无关联。这只是一个几乎与本·拉登一样疏忽人命的人,选择就义素不相识人的性命以获得免费的媒体关注。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美国的全国性媒体可以自由地报道它们爱好的任何事件,它们对琼斯先生的行为却视而不见,这极好地提醒了什么是美国。很显然,这一行为在受到阿富汗领导人的谴责之前,世界上根本就没人注意它。我一点也不信任琼斯先生是一名基督徒。我认为他是一个爱好表演的人,一个作秀者,制造某种马戏表演,从而会吸引媒体的注意力,让他自己走红。
《法治周末》:你有信奉伊斯兰教的朋友或者一般熟习的人吗?与他们如何相处?
史蒂夫·莫拉夫:我最近没有这类朋友。我过去有过,而且伊斯兰教与我们的友谊无关。
《法治周末》:你如何对待本·拉登和塔利班时期所推行的极端思想?
史蒂夫·莫拉夫:美国过于简略地把本·拉登和塔利班看成美国公敌。其实多数美国人知道,本·拉登们作为恐惧主义者,在世界上失道寡助。但多数美国人可能没有察觉到,本·拉登和他的同伙实际上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政府的敌人。本·拉登被击毙后,最隆重的庆典可能就发生在中东国家的领导人的宫殿里,那些国王们认为自己总算稍微安全些了。当然即使本·拉登的兄弟姐妹们也可能私下庆幸终于解脱了他。本·拉登来自一个非常富庶和胜利的家族,但毫无疑问,这个家族的名声都被他毁了。
《法治周末》:你信仰何种宗教?是否对所信仰的宗教具有优胜感?美国一向以对各种文化的包容而骄傲,你能感受到自己的宗教或文明与其他宗教或者文明发生冲突吗?
史蒂夫·莫拉夫:作为一个犹太人,我自己的民族群体在美国人口中仅占很小的比例。然而我从未经历过任何有关我的"民族遗产"的显著冲突,尽管与许多犹太人一样,我不信奉我自己的宗教犹太教,也对它不感兴致,而且我也不信仰任何宗教。我以前曾在美国的一所为伊斯兰国家外交官的子女传授教育的学校里教过书,即使在那里,我也没有认为因为我是犹太人这一事实而成为讨厌的对象。
大多数美国人很少有优胜感,原因要么是基于他们的宗教,要么是基于美国在世界上的位置。然而人们都有情感,像眼下这个时候,以及本·拉登袭击美国的时候,许多美国人都居高自负以优胜感自我抚慰。这是很自然的进程,但我以为美国人民对多种文化的高度容忍值得赞美。大多数美国人马上意识到这些袭击也同时杀死了穆斯林教徒以及信奉其他宗教的人。
美国既是许多文化的熔炉,也是它们的避风港。在"9·11"袭击之后,在我的家乡纽约州的绮瑟佳,许多人马上走到一起以示团结,展现我们美国人不能因这些卑劣的手腕和手法而四分五裂的决心。这些集会中也包含穆斯林教徒,他们受到了所有人的欢迎。
有些美国人确切以为他们的宗教更为优胜,也以为美国事一个更为优胜的国家。我个人的观点是,每个社会都有必定比例的人须要认为自己比他人优胜。我以为这些人自身所持的价值观不高,因此他们试图从他们的国旗中寻找慰藉。
《法治周末》:
你去过哪些国家?在你看来,哪些因素造成了国家之间的误会与敌对?又是哪些因素促成了国家之间的良好关系?
史蒂夫·莫拉夫
:我信任国家之间的仇视是由政客们制造的,他们利用其大众的无知而捞取利益。当两个国家的大众互相仇恨时,政客们能通过将敌对国家妖魔化来获得支撑。
然而在美国,只有极少数足够无知的人才信任这一点。大部分美国人以为他们将工作拱手让给中国人是因为美国工人懒散,而且他们尊敬并钦佩中国人勤劳的本性。
这种无知可以通过两国间的交换拜访来清除。目前,美国大学里有大批来自伊斯兰国家的学生。在美国研究生班级中,几乎有一半的学生是外国人,这些人又都来自不同的国家。每30人中便可能有10个国家的人。这给美国在全世界提倡和平与宽容供给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这些来访者给美国人带来了新的视角,也给他们的国家带来了对世界更普遍的认知。外国人回到母国后会对美国持友善的态度,而出国的本国学生也担负了亲善大使的角色。中国政府可能应当动用一部分宏大的美元储备,派遣甚至更多数量的年青中国学生去美国。
美国也有项目赞助美国学生去其他国家以及外国学生来美。然而,这些项目在其全体存在期间的费用,也许还不够支付近年来战斗中一个月的军事行动的费用。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就是在这样一个项目下,作为罗兹学者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就读。
意大利以及其他欧洲国家总体上已变得越来越喜好和平、越来越友善。他们在欧盟的参与活动已发明了一种全球公民的感到。
很多美国人曾以为,在南斯拉夫的国家政府跨台后,不同的派系永远不会获得安定,因为他们的冲突已达数百年之久。然而,数百年来,法、意的这一边界也曾目睹各式各样的战斗,而现在似乎没人会在意这一边界划在哪里。倘若我当时从路上往旁边走10米,我都不会知道我身处哪个国家。南斯拉夫现在也获得了和平,穆斯林教徒与基督教徒肩并肩地生活。
我在俄罗斯待过一些时间,我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当年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那时,我的国家与他们的国家在一个冲突上筹备摧毁全世界,而那个冲突的结果是任何一方都没有胜负。
而今冷战已经停止,结果是什么呢?我的观点是,美国事当今最为社会主义的国家,中国处在中间,俄罗斯则继续它的纯资本主义的实验。我以为,欧洲是所有这些地区之中最为社会主义的。冷战有什么用?
(感激胡小倩博士对采访供给的支撑)
- 上一篇:短期shibor利率止跌回升--中国国情网 【加入收藏】
- 下一篇:存准率不存在绝对上限--中国国情网
相关链接
- 汽交总:气价狂飙百上加斤--中国国情网
- 人民币国际化再引海外关注 十年内或成储备货币--中国
- 刘明康委员:民间借贷一定要立法--中国国情
- 赵斌:加大对科技型中小企业支持力度--中国国情
- 白立新:商业伦理不仅是道德问题,更是战略问题--中国
- 小微减负--中国国情手册
- 2012中国经济在顿挫中前行--中国国情网
- 资本项目开放定下十年限 央行报告认可条件基本成熟--
- 中国CFO对经济现状最有信心--中国国情
- 刘永好:加大金融支持“三农”企业力度--中国国情
- 刘汉元:尽快出台《放贷人条例》--中国国情
- 进一步加大对贵州的金融支持力度--中国国情网
- 大连资本市场今年好戏连台--中国国情手册
- 部分种类地方融资平台贷款展期松动--中国国情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