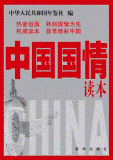热点推荐
- ·男子因婚姻矛盾持刀砍伤妻子岳母潜逃
- ·山东公开选拔15名副厅级干部 1000余
- ·山东荣成投资千万改善大天鹅栖息地环
- ·村委村民一起挖卖300余棵古银杏树(组
- ·展览馆回应招讲解员要求博士学位称拟
- ·青岛举办海葬活动 923名逝者魂归大海
- ·青岛四方区中小学推广武术操--中国国
- ·山东菜农自杀调查:投资养羊失败曾三
- ·幼儿园老师被指体罚虐待孩子被开除
- ·李法泉被任命山东省纪委书记--中国国
- ·高一男孩爱好坐火车走遍20城市 攒500
- ·济南慈善超市面临生存困境:顾客流量
- ·山东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950元--
- ·工业和建筑业--中国国情手册
- ·9人乘面包车被困漫水桥获救 车被冲进
- ·青岛载56人大巴翻到桥下 16名被困者
相关链接
入编邀请更多>>

2010版国情
乡村医生工作45年为养老问题发愁(图)--中国国情手册
2011-04-11

文/片 本报记者鲁超国
做了45年乡村医生的徐玉伦,年过七旬却开端为自己的养老问题犯愁。像徐玉伦这样的乡村医生全国还有102万人,大都年过半百,是时候斟酌他们的养老问题了。
“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必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近几年来,泰安市东平县戴庙乡中金山村70岁的乡村医生徐玉伦一直想找个合适的渠道,说说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河南村医马文芳议案解决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这让徐玉伦重新燃起愿望。
春节前一连26天,60岁的马文芳乘坐长途汽车、公交车行走于河南、山东、湖南三省的100个自然村,共访问了100位乡村诊所医生,其中就包含徐玉伦。
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就是彻底的农民了
徐玉伦的卫生所,临近主街,没有挂牌子,甚至连一个标记性的红“+”字都没有。
“村里人都知道,不用挂牌子。”房子是近年新建的,钱是由徐玉伦的子女凑的。“以前的房子成危房了,在山上,村民去找我看病也不便利。”徐玉伦说。
房子从外面看上去还比较“场面”,堂屋三间,西侧房屋是蕴藏室,里面堆放着一些农具,还有一个铁皮的粮囤,算是最值钱的“家底”了;东侧两间房,一间是厨房,一间是卧室,没有客厅。
临街的两间东屋,就是徐玉伦的诊所了,药架上摆满了药,桌子上堆放着一些医学书籍。墙角处堆放着几十块煤球,“天冷的时候才点炉子,防止药冻了,失效了就麻烦了。”
诊所的墙壁上挂着“新农合定点医疗”的牌子。
平时,他的诊所门是关着的,“一天来不了几个人,我不能老在这里靠着,地里有活的时候还是得下地干活,有人生病了就到地里去叫我。”
看到记者嘴上长泡,徐玉伦说:“你这是上火。”说着,从药架上找出一盒药,倒上水让记者服用。
“你看到了吧,你来这么长时间了,一个来看病的都没有。”徐玉伦拿出一盒药,“这一盒药好几块钱,只有1毛钱的利。我还不收诊断费。”
徐玉伦说,有时候他一天接不到一个病号,也有可能一天来两三个,“一个月也就100多块钱的收入。”为保持生计,他还要下地,靠3亩地种植小麦、棉花和南瓜生活。
“还真不如开个小卖部,至少不用承担如此高的风险啊。”但他舍不得就这样把自己一辈子的“手艺”丢了。
当然,有更多的人不想脱离乡村医生这个队伍,否则,就是彻底的农民了,他们之所以一直在坚持,是愿望有朝一日国家能够给“乡村医生”一个说法。
徐玉伦一直在期待一个消息:“第10235号议案立案没有?上面有没有什么回答?啥时候给回答?”
他清晰地记得,3月3日下午3点10分,北京的一个记者给他打过一个电话,讯问行医的收入情形、种地的情形等,他知道,这应当是马文芳在两会上议案的功绩。
今年春节前,马文芳曾找到他,调查关于乡村医生的现状。
马文芳是一位名人。他是河南省通许县大岗李乡苏刘庄村村民、乡村医生,行医42年。
马文芳头上的光环很多:全国劳模、全国优秀乡医、全国健康卫士榜样、2008年北京奥运会火把手、激动中原人物,曾受到胡锦涛总书记和温家宝总理的接见……
但是,最让马文芳觉得骄傲和管用的还是“全国人大代表”的头衔。今年的全国两会,他已经是第四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呼吁关注乡村医生的待遇和养老问题了。
以前的3次呼吁都没有引起看重,他以为是“很多人不了解这个群体”。
于是,今年春节前,他自费对乡村医生进行了访问和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让马文芳忧心忡忡,“在调查的100个乡村医生中,年纪最大的78岁,最小的53岁,平均年纪63.14岁;行医时间最长的60年,最短的31年,平均43.6年;月收入最高的1000元,最低的50元,平均月收入342.7元;身体健康的84人,有各种疾病的16人。”
“乡村医生队伍后继乏人,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正面临着‘人走网破’的威逼。”马文芳直言,而这些卫生所还要担当着公共卫生服务,担当着村民的健康管理。
今年33岁的褚衍栋,从枣庄市卫校毕业后,一直在故乡的卫生室一边行医一边种地,他曾告知马文芳,“每年收入四五百块钱,养老也没有保障,不想再干了!”
据统计,目前全国乡村医生共有102万人,担当着农村防疫、医疗、保健、协助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处置等工作。
马文芳的议案,受到了很多乡村医生的关注,这其中就包含行医45年的徐玉伦。
“议案提交后得三个月之后才给回答。”马文芳告知本报记者。也许,没有人比他更想知道答案了。
“赤脚医生”在农村曾很有面子
徐玉伦入行行医,其实很偶然。
“当时全部大队1000多号人,就两个卫生员,一个70多岁了,一个年青的业务还不是很熟练,根本不够用啊。”
1966年,初中毕业的徐玉伦被推举去卫生院。全部大队当时也只有5个初中毕业生,这已经算是高文凭了。徐玉伦也有去从军的机遇,但他放弃了,“我认为还是在农村锤炼好。”
有材料显示,1965年,中国有140多万名卫生技术人员,高级医务人员80%在城市,其中70%在大城市,20%在县城,只有10%在农村,医疗经费的投入农村只占25%。
1965年6月26日,时任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组数字汇报给毛泽东后,毛泽东震怒了:“卫生部不是人民的卫生部,改成城市卫生部或老爷卫生部,或城市老爷卫生部好了。”
毛泽东指示:“应当把医疗卫生工作的重点放到农村去,造就一大量‘农村也养得起’的医生,由他们来为农民看病服务。”
根据毛泽东的进一步指示,普及农村医疗卫生工作在全国敏捷展开,一个“半农半医”的群体由此敏捷突起。
徐玉伦正是那个时期的产物,经过几次培训之后,他开端背起药箱为群众看病。
而“赤脚医生”则是农民自发叫起来的,因为南方的农村都是水田,只能赤脚下田,所以赤脚就是劳动的意思,“赤脚医生”就是既要劳动也要行医。
“那时候挣工分,一个月有多少天,我们就会拿多少天的工分。哪怕是大年初一,有人生病了,过
来叫,也得去。”那时候也没有“加班”的说法,徐玉伦曾经一晚上被叫起来七八次,“我都不敢脱衣服睡觉。”
“新中国成立初期,疟疾、麻疹、天花等沾染病风行。”徐玉伦天天提着壶、端着碗、拿着药,挨家挨户去送药。“看到药咽到肚子里了才走。”
疟疾的根源是蚊子,徐玉伦回想说,当时他在村里村外逐个水井、地窖、山洞熏灭蚊子。“现在,这些沾染病都没有了,你说说是谁的功绩?”
辛劳虽辛劳,可是徐玉伦认为这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
那时候,“赤脚医生”在农村是“很有面子”的岗位,村民对“赤脚医生”十分尊敬,医生在村里的位置很高,甚至要超过村干部。谁家来了客人请“赤脚医生”去作陪,客人和主人都会认为是件很光荣的事。
1968年9月,当时中国最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红旗》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从“赤脚医生”的成长看医学教育革命的方向》的文章,1968年9月14日,《人民日报》刊载,毛泽东在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批示“赤脚医生就是好”。随后《文汇报》等各大报刊纷纭转载。“赤脚医生”的名称走向了全国。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赤脚医生”手册》的发行量仅次于“毛选”。
1985年初,卫生部作出停滞使用“赤脚医生”这一称呼的决定,原来的“赤脚医生”要进行考核,合格的将被认定为乡村医生,取得从医资历后可以继续行医。“赤脚医生”的历史至此也就停止了。
当时,徐玉伦所在的村庄里共有三名“赤脚医生”,通过了考核之后,分道扬镳,自营生路。
“孪生兄弟”的不同命运
徐玉伦提起同村的王兴勤、李守枝和方芝兰(音),语气酸酸的,“他们比我小,早早就退休了,现在挺舒畅,平时漫步、打牌,很安闲,每个月领着将近3000元的退休金。”
他口中的这三个人,都是当年的民办教师,和“赤脚医生”一样,都是我国在必定特别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多年来一直享受同期待遇,有人称之为“孪生兄弟”。
1979年10月,国务院决定将全国136个边疆县的8万余名中小
学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揭开了党和政府妥当解决民办教师问题的序幕。
1994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党中央、国务院明确提出,“争夺到本世纪末基本解决民办教师问题”。解决民办教师问题从此有了历史性的转折。
1999年至2000年,全国有25万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民办教师逐渐退出讲台。
民办教师问题的解决,让乡村医生感受到了不公和冷落。
同为“孪生兄弟”,境遇为何如此悬殊?
一位曾经的民办教师以为,很多乡村医生没有斟酌或者有意躲避一个问题:“包产到户后,赤脚医生改变成乡村医生,在这个进程中他们的身份已经悄悄发生了根本的变更。与民办教师不同,乡村医生已经‘市场化’了,靠‘手艺’来赡养自己,而且有个别医生赚得还不少。而民办教师呢?不可能靠收孩子的学费来赡养自己吧?”
“大家各干各的,挣一块花一块,挣不到就只能靠地里刨食。”徐玉伦也说,为了多赚钱,有个别的乡村医生也变了味,“啥病都能看,啥病都有‘祖传秘方’,开端学会忽悠人了。”
但是,乡村医生依然承担着很多公共卫生服务的职能。2003年,非典期间,戴庙乡医院召集开会,徐玉伦接到了一个任务:为回乡务工人员测量体温。
“当时乡医院只给了一件白大褂,一个口罩,如果沾染的话,首先是我,但是人命关天。”徐玉伦没有撤退,因为他以为这是他的职责。
徐玉伦忙了三个月,非典停止后,他去医院要钱,医院让他去村委会要,村委会则称没有这方面的开支,结果他没有得到一分钱的酬劳。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时候他们防疟疾、灭蚊子还有工分,现在遇到了相似的情形,徐玉伦却不知道该找谁要钱。
“赤脚医生”老了盼望“穿上鞋”
去年9月份,徐玉伦写了一份《干了一辈子农村医生老来无人管》的文章,“写好之后我专门找了个大学生看了看,内容没犯什么错误吧,犯错误的事情我不干。”他把这篇文章邮寄到北京一家报社,却如泥牛入海。
从2008年开端,戴庙乡的一些老乡村医生就推举他为代表,为大家奔忙呼吁养老问题。
他不想被戴上“越级上访”的帽子,因此从乡医院开端,县、市、省卫生部门逐级反应。
“苦我吃了,贡献也做了,该说的我必定要说。说不说是我的事,办不办是你的事。”他说话很勇敢,但是他办事很谨严,担忧犯错误毁了自己一辈子的清白。
马文芳的涌现让徐玉伦看到了愿望。马文芳以为,要解决乡村医生的后顾之忧,国家应尽快出台乡村医生养老保险指导看法,明确乡村医生身份,将乡村医生的人事关系纳入乡镇卫生院管理,供给必定工作经费和人员工资,保障工作人员基本生活。同时逐步树立乡村医生养老保险、聘请与退休制度,切实解决乡村医生老有所养的问题,这样才干筑牢农村三级卫生服务网络的网底。
今年4月初,有媒体报道,山东省政府将采用以政府购置服务等方法多渠道加大对乡村医生的补贴力度,部署必定比例的基础公共卫生服务工作由村卫生室承担,对所需经费,依照政府购置服务、绩效考核、以考定补的原则,从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经费中按不超过30%的比例兼顾部署。
去年11月份,徐玉伦去了一趟北京,去找他的一位初中同学,目标就是看看这位同学能不能帮他解决老有所养的问题,“以前的同学都比他混得强”,徐玉伦的老伴插了一句。
那是他第一次去北京,经过天安门时,他驻足,盯着毛主席像,仿佛看到了自己年青时背着药箱,意气风发地走在乡间小路上,村民们热忱地挥着手向他打召唤……
(编辑:SN026)相关链接
- 山东5年查处厅级以上干部78人--中国国情手册
- 军官智救六名落水游客负伤 向单位请假不提救人--中国
- 公交女司机人工呼吸救发病小伙(图)--中国国情
- 山东临沂大学165名学生发生腹泻--中国国情手册
- 山东首富自办电厂电价比国家电网低1/3--中国国情手册
- 山东第十次党代会24日开幕 将选举十八大代表--中国国
- 青岛将取消教师资格终身制全面推行聘用制度--中国国情
- 山东将启动10段齐长城抢救性保护和展示工程--中国国情
- 山东规定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950元--中国国情
- 专家称异地高考难解决根本在于户籍制度--中国国情网
- 医院诊疗不当致肾结石患者成植物人赔出216万--中国国
- 张江汀当选山东烟台市委书记--中国国情网
- 女子因未获工伤赔偿欲跳海遭遇退潮--中国国情手册
- 男子微博寻女获众网民转发后改口称已找到--中国国情网